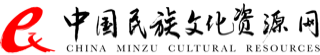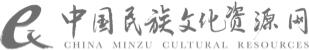做汉藏文化交流的使者
讲述人:孔宪岳
时间:2005年12月30日[按莫老师意见改]
地点:北京 民族出版社
一、努力掌握翻译技巧,在实践中学习、进步
我出生在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朵什乡一个有名的藏族家庭,我的藏文名字叫南卡桑格。小时候父亲把我送到私塾读书,私塾的老师教得很好,他把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著作,一句一句、一字一字地给我们讲解,再加上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学得也认真,所以汉语的基础打得很扎实。
1952年西北民族学院成立语文系,我考入西北民院语文系的藏语专业。我在大学4年学习的完全是藏文,那时学校里除了老师的藏文讲义以外,看不到任何藏文资料,甚至连藏文报纸都没有。为了学好藏语,我就把老师的讲义一句一句记下来,反复背诵。经过这样的努力,到大学毕业时虽然我的家庭成分不好,但是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学校还是将我分配到北京的民族出版社藏文编译室工作。
那时,民族出版社汇聚了许多少数民族高级知识分子。像我们藏文室的丹巴嘉措、多吉杰博、索朗多杰等老前辈,他们的学问做得都非常好。刚刚走出校门,又来到这样一个学者荟萃的地方,我十分兴奋,抓住一切机会向各位前辈学习、求教。我刚到出版社时,只会讲“安多”语,“安多”语是藏语方言之一。虽然在书面表达上“安多”语与相当于藏语中“普通话”的“拉萨”语相通,但在口语表达上却有着很大的差别。通过几年的努力学习,我完全掌握了“拉萨”语。后来,我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同声传译”工作,就是用“拉萨”语完成翻译的。
从1955年我来到民族出版社,经过将近10年的学习、实践,我们这些年轻人也渐渐地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承担主要的编辑、翻译任务。在这期间,我在藏文编译室翻译组前后翻译出版了《跟随毛主席长征》、《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政治常识读本》、《祖国的花朵》等10多万字的图书。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各种政治运动不断,但我始终没有中断学习,每天坚持看书学习,因为俗话说:“学而后知不足”,只有坚持学习,才能不断进步。
“文革”开始了,整天都在开会,白天的时间都被白白浪费掉。可是社里还有一些期刊、图书的出版任务,我们这些翻译编辑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做业务工作。为了翻译出高质量的好书、好文章,我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藏文、汉文两种语言。我把汉文的二十四史从《史记》开始,包上《毛泽东选集》的封面,白天开会时我就坐到会场的最后一排,躲开人们的视线,一本一本地往下读。晚上遇上不加班,我就回家看藏文书籍。
1974年,上边提出要评《水浒全传》,批判“宋江投降主义路线”。因为《水浒全传》没有藏文版,上边就要我组织人员翻译藏文版的《水浒全传》。因为是供批判之用,所以领导要求藏文版的《水浒全传》只要能看懂就行,不用翻译得多好。当时我就想:“这些浮躁的批斗风不会长久,可是《水浒全传》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它的内容和魅力却是永恒的。如果翻译好了,一定会对汉藏文化交流起到很大的作用。”因此,在组织翻译的过程中,我向参加翻译的人员多次强调,翻译一定要忠实原文,做到“信、达、雅”的基本准则。这部译著大约经过两年时间才译完出版,这时候批判“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高潮早已过去,而这部译著在整个藏区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促进汉藏文化交流、普及藏语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部译著以后还获得了西藏自治区颁发的翻译图书一等奖。
在翻译《水浒全传》的基础上,我又翻译了另一部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上半部,出版后也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二、与“石头海螺”结缘,做了人生中的一件善事
“文革”结束后,当时的国家民委副主任杨东升同志当选为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要去西藏赴任,国家民委调我担任杨东升同志的秘书兼翻译一同前往西藏。杨东升同志是位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我记忆中的他总是穿着一身虽然半旧却十分干净的衣服,脚穿一双布鞋。杨东升同志生活十分简朴,工作起来却是特别认真。我在西藏担任杨东升同志翻译的大半年时间里,跑遍了西藏除阿里以外的所有专区和县城,跟随他下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一次,我们下到林周县的达隆寺调研,达隆寺是七八百年前修建的噶举派的有名寺院。“文革”期间,西藏的文化被破坏得很严重,很多寺庙都被拆掉了,达隆寺当时也是一片废墟。杨东升同志看到这些景象心里很难受,要我将这些情况写成详细报告上报。我走到废墟中仔细察看,发现在满地的石头瓦块中有块石头形状十分奇特,像个海螺,大概一两公斤重。我就顺手把这块石头捡了起来,放到我随身带的包里,带回了拉萨。后来回到北京,我将这块“石头海螺”放到一个玻璃盒子里,摆在书架上。
大约七八年后的一天晚上,我在电视新闻上见到西藏达隆寺修复的报道,我一下子想到了那块“石头海螺”。于是我马上给达隆寺的活佛孜珠仁宝写信,将这块“石头海螺”的形状以及捡到它的时间地点详细地告诉他,并问他这个“石头海螺”是否对他们有用。很快,我就收到了孜珠活佛的回信。他告诉我这块“石头海螺”是达隆寺的镇寺之宝、神物,因为有了这个“石头海螺”才有了达隆寺,孜珠活佛还说要立刻派人来迎回“石头海螺”。当时我考虑:从拉萨到北京这么远的路,来一次谈何容易;况且达隆寺刚刚修建恢复不久,派人前来迎接花费不小。于是我马上回信,说既然“石头海螺”是达隆寺的神物,你们不要着急,我会托付可靠的人、以最快的速度将神物送回。那时我是藏文编译室的主任,恰好同室的翻译阿旺同志要回拉萨,我将“石头海螺”托付给他,嘱咐他一定要原原本本地把“石头海螺”交到孜珠活佛的手中。阿旺将“石头海螺”带到拉萨,恰巧在达隆寺驻拉萨办事处遇见了孜珠活佛。孜珠活佛见到“石头海螺”,泣不成声,从达隆寺召来僧队隆重地迎接“石头海螺”归寺。后来孜珠活佛到北京来开会,还特地要了一张我的照片,拿回达隆寺和“石头海螺”供在一起。我现在回过头想想,觉得也是奇怪,当初为什么捡到这块石头,而且捡到后一直供在家里,最后又能将“石头海螺”送归了达隆寺?这也是我结下的一点佛缘,做了人生的一件善事吧。
三、担任藏文编译室主任,配合十世班禅出版藏传佛教图书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已经进入了80年代,民族出版社的工作也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这时我担任的是藏文编译室主任工作,在担任室主任期间,我与十世班禅有了一些接触。
上世纪80年代十世班禅成立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专门深入学习和研究藏传佛教。十世班禅组织高僧大德编好了数十万字的7部教材后,把我叫去亲口对我说:“我有7本教材,你把它3个月内出版完毕,不要影响佛学院的开学。”3个月出版数十万字的教材,时间是十分紧张的。于是我回来以后和领导商量,把手头上的其他工作全部停下来,集中精力就出这7本书。7本教材在3个月内按时出版了,十世班禅很满意,以后他又组织藏族学者编纂了很多图书,比如藏传佛教四大教派的传承史等等,我们都一一编辑校对出版,成为研究藏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民族出版社出版宗教图书是在宣扬宗教迷信,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个老师还把我告到统战部,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宣传宗教迷信的书籍,毒害群众。统战部派李国清来了解情况,李国清曾在西藏工作过多年,是位了解藏族文化和宗教的专家型的干部。我向李国清汇报说:这些书籍对藏传佛教来说都是基本教材,不能说是毒害群众。他听了汇报以后也认为没有问题,说还可以继续出,这件事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大的支持。
一次,我去十世班禅那里,看见他正在阅读《扎什伦布寺寺志》,《扎什伦布寺寺志》是用竹笔写在单张纸卷上的,于是我就向他提出把这本书照相制版出版,以免《扎什伦布寺寺志》被损坏而失传。《扎什伦布寺寺志》出版以后,十世班禅很高兴,他说:“自从佛学院成立以来,你配合我们出版了许多教材和图书,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我现在回扎什伦布寺为前几位班禅的灵塔开光,回来后我好好地奖励你!”没想到这位爱国爱教的大活佛却在完成了开光仪式后,过早地圆寂了。
1992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除了担任由中央统战部主办的《中国西藏》藏文版的编审工作外,我将主要精力用在学习和翻译密宗经典方面。这十几年间,我翻译了藏文密宗经典20多部,约40多万字。
如今我已年逾古稀,回想一生的经历就像是做了一场长梦。“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我不会虚度剩下的年华,尽力将我所学的有用东西发挥出来,留给后人。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2006-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