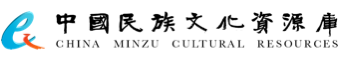

河煌谷地。资料图片
“西北民族走廊”是上世纪80年代初由我国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首先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是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费孝通所提出的“西北民族走廊”由两条走廊构成,即“河西走廊”以及与该走廊呈丁字形、从祁连山脉向南直至横断山区(即藏彝走廊地区)的“陇西走廊”。西北民族走廊的形成受到自然、历史、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古代丝绸之路有一定的联系。当前,学术界针对“西北民族走廊”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有许多未开发的领域等待研究。
一、“西北民族走廊”的概念与范围
学术界普遍认为,费孝通提出的“西北民族走廊”由两条走廊构成,不仅包括从甘肃到新疆的这条历史上著名的“河西走廊”,同时也包括与该走廊呈丁字形、从祁连山脉向南直至横断山区(即藏彝走廊地区)的呈南北向的“陇西走廊”。
1982年5月,在武汉华中工学院社会学研究班和中南民族学院部分少数民族学员座谈会上,费孝通首次提到西北民族走廊:“西北地区还有一条走廊,从甘肃沿‘丝绸之路’到新疆。在这条走廊里,分布着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等,他们是夹在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中间。有的信喇嘛教,有的信伊斯兰教;有的讲藏语,有的讲蒙古语,有的讲突厥语,……有些民族讲两种语言。”根据这一描述,费孝通所指的这条走廊是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丝绸之路。1985 年,费孝通赴甘南藏族自治州考察期间,提出了“陇西走廊”的概念,指的是连接甘肃、青海两省的地区。1997年费孝通在其翻译的《甘肃土人的婚姻》一书的序中,又提到了“从甘肃西北部沿祁连山脉向南延伸到沿甘肃边界和四川北部”的“那一条民族走廊”。
西北民族走廊深居内陆腹地,自成一个内部体系完整的地理区位。从地缘上看,它属于山地高原区,处于我国地势的一、二级台阶,并且正好处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边缘和交汇地带。根据自然地貌特征以及当地的经济类型,西北民族走廊大致可以分成4个自然区域:一是河西走廊,处于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分界线上,东起乌鞘岭,西至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南靠祁连山,北依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南北宽数十至百余公里、东西长约1000公里。河西走廊是中西陆路交通与东西民族走廊的咽喉之地,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二是河湟谷地,位于青海东部(日月山以东)和甘肃西部(包括今天的兰州市及临夏回族自治州全境)。这里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也是历史上所谓“河湟地区”的核心区域。河湟谷地气候相对温暖,宜耕宜牧,农业相对发达,是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长期争夺的地方,现在也是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地区。三是甘南草原,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甘肃西南部,是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活动频繁及繁衍生息的地方,经济类型以畜牧业为主。四是洮岷山区,是青藏高原和秦岭山脉的一部分,包括陇西和陇南部分地区。其中,陇西地区处于黄土高原西部,适宜发展农业,是陇西地区农业生产的精华地区。陇南山区是秦岭山脉的西延部分,以山地及河谷农业为主。这里曾是古代氐、羌民族活动的重要区域。
西北民族走廊同时是一个人文区域概念,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我国历史上汉唐文化的中心,是开发较早、人口众多、文化多元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正因为此,著名学者季羡林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 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 再没有第二个。”
二、“西北民族走廊”与古代丝绸之路
谈到西北民族走廊,人们会不自觉地联想到丝绸之路。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西北民族走廊中的河西走廊经常被人们视作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根据上文所述的地理范围,笔者认为,西北民族走廊大致相当于北方丝绸之路的国内部分。
北方丝绸之路由西域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构成。其中,西域丝绸之路是张骞通西域以来形成的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干道,起自西汉首都长安(今西安),经陇西或固原向西到金城(今兰州),依次通过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出玉门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由此分为南北两道。南北两道会于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的犁靬(埃及亚历山大城)。草原丝绸之路大体分南北两道,南道即东汉收复伊吾(今哈密)之后开通的线路“敦煌—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昌吉—伊犁”。北道是伴随着北匈奴为首的各北方草原民族西迁而逐步形成的通道,包括东起西伯利亚高原,经蒙古高原向西,过咸海、里海、黑海,直达东欧的欧亚草原,这条通道在辽金和蒙元时期最为兴盛。
综上所述,西北民族走廊的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北方丝绸之路的国内部分。但二者又有明显的区别。北方丝绸之路开通于汉代,在时间上晚于西北民族走廊的形成。虽然西北民族走廊的概念是在当代被提出,但其作为实体早已存在于历史,它的形成与发展起源于民间交往。而丝绸之路的开通源于政治、军事的需要,是在政治、军事力量主导之下形成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后来发展为以丝绸贸易为主的通往西域及欧洲的国际贸易交通线。伴随着丝路贸易的开展,丝绸之路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各民族不自觉地进行了文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交流。在丝绸之路上发生的文明碰撞与交流,很早以前在西北民族走廊上就演绎过。不同的是,西北民族走廊的文明交流与碰撞仅限于国内或王朝周边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与碰撞,而丝绸之路上的文明碰撞与交流由国内延伸到了国外。
三、“西北民族走廊”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研究西北民族走廊,对于促进当前西北民族走廊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愿景实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学术界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对西北民族走廊展开研究:西北民族走廊概念的界定,西北民族走廊的范围、地理特点、生态环境与交通研究,西北民族走廊中的民族交往与融合研究、经济开发研究、宗教及民族文化研究,西北民族走廊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研究,西北民族走廊的形成原因探究等。围绕这些问题开展的研究成果,有秦永章的《费孝通与西北民族走廊》《西北民族走廊的人文地理特点》,马宁的《论“陇西走廊”的概念及其内涵》,李星星的《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陈庆英、赵桐华的《关于西北民族走廊的思考》,葛政委、黄柏权的《论民族走廊的形成机理》,马成俊、王含章的《中国民族走廊与国际民族通道:另一种视角看丝绸之路》等。
从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及研究视角考虑,笔者针对西北民族走廊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以下两点:
首先,要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西北民族走廊展开研究。从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上看,现有的西北民族走廊研究成果中,理论和方法相对单一,仍主要以民族学研究为主,以定性研究为主。西北民族走廊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这就要求相关学者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应注重多样性。综合运用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西北民族走廊展开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此外,还需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和软件,加强对西北民族走廊的量化研究。通过多学科研究,通过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可以使得西北民族走廊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
其次,要进一步扩展西北民族走廊的研究领域,转换研究视角。目前关于西北民族走廊的成果中,事实论证居多,对该民族走廊的特点和理论分析还不够深入,该民族走廊与其他民族走廊比较研究方面的成果更是寥寥无几;历史方面的研究较多,对该民族走廊在当代的发展问题关注不够;对该走廊自身的研究较多,对其历史成因及其对国家、民族所起的作用研究不足。应将西北民族走廊研究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如西北民族走廊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西北民族走廊的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西北民族走廊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西北民族走廊的地区整体规划与发展布局、西北民族走廊发展与国家“一带一路”愿景的实现等,这些都是学术界今后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民族走廊与历史上形成的丝绸之路紧密连接,在多元族群交往互动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影响着我国的民族关系格局,也影响着我国与周边各民族国家的关系。在推动“一带一路”愿景实现的过程中,相关学者应该以国内民族走廊研究为基础,以更广阔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视野,结合国内现有研究和海外民族志研究,为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学)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016BJMZTJJY0209)。】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